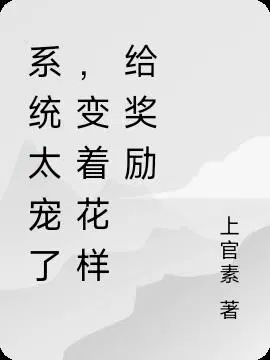柳千重现在是一门心思想还女儿一个清白,一旦他的女儿罪名被坐实,何止是对她一人有影响,连带着他自己也会被冠上教而无方的恶名。
如今廷尉署他插不上手,于是他下朝之后,命人去接触了封尤眠,既然推人之说是从封尤眠这里传出来的,那他就有作证的义务。
结果封问心吩咐去查封尤眠的人就查到了,只有柳千重派人与封尤眠接触过。
这在封问心看来,封尤眠作妖的底气竟是来自柳千重。
封问心怒极反笑“老匹夫尔敢。”
竟然把手伸到封家里面来兴风作浪了,既然如此,那他也不必顾念柳氏了,反正有她爹为她保驾护航。
柳氏被从园子里请出来时,封问心都没有与她多说一句话,直接让人将她带走了,她到廷尉署也并没吃上茶,而是下了廷尉狱,这里做为最高司法机构向来只关达官贵人,若不是她身为宰相夫人,就这种案件都够不上廷尉署的边。
柳氏还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当时听说是廷尉署来请她走一趟,她便以为是她父亲派的人来,想都没想便跟着走了。
觉得白氏是自尽,即便她有错也罪不致死。
她来到廷尉署后并没有人审她,就被直接下了狱,起初还闹着要见柳千重,与那些狱卒逞狠,直到封应时的那个庶女也被人带了进来关在了旁边。
柳氏心中一松,认为定是她父亲帮她找来脱罪的。
那小姑娘是封应时唯一的女儿,虽是庶女,也是锦衣玉食娇宠着长大的,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本就终日惶惶不安,进来后一直哭哭啼啼,见到柳氏也不打招呼,一双泪目中反而带着怨恨。
只因她来时的路上听随行的皂吏在议论,说是事件影响恶劣使得陛下震怒,一旦查出是何人致白氏死亡,是要闹市杀头平民愤的。
又说柳大人当庭否认是柳氏之过,而封相也默认了。
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无聊到要当着嫌犯的面说这些不实的话,那得问问傅雪。
小姑娘本就胆小,越听越怕,觉得自己定是被拿去问罪斩首的,虽然自己有错,但若非柳氏先嘲讽封尤眠家的小娘子,又虐待白氏,她哪来那个胆量伸手推人,也就根本酿不出这般祸事。
说到底,她随着柳氏一同瞧不起别人,便恶向胆边生,等到祸事上身,才又来怨怪别人给了她胆量做坏事。
这件案子如今查的是白氏的死因,她怎么死已经不大重要了,因何而死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妻虐妾自古以来再是寻常不过,但北阴,是尊女君的国家,对女子本就比其他的国家要更宽容一些。
只有那些位高权重的高官后宅,还保留了这种不把妾室当人的劣根性。
所以白氏之死,在相府根本没被当回事,但这样的事,拿到明面儿上来说,绝对是戳平民百姓的痛点的,因妾多来源于百姓,没有高门大户的女子会给别人作能任意发卖的妾。
但柳氏和她父亲一样,不明白其中的关键,总觉得白氏不是她亲手杀的,她就不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封问心待廷尉署走后,立即着人备下马车前往封应时的宅邸,想着既然要舍弃柳氏,那就要保全二弟家的那个庶女。
谁知他到了地方,才知道有另一批人已经将那庶女带走了,按路程远近来看,廷尉署去相府请柳氏与来此请那个庶女几乎是同步的。
这就很有趣,案子都没审,没人告状也没人提供线索的情况下,廷尉署怎么就想到要去请这个庶女了。
除非是柳千重授意。
但柳千重不是该回避么?
难道他当真是拼了这顶乌纱也要将他的女儿保下来?
廷尉署来请人时,封应时还想负隅顽抗,仗着家世不肯交人。
但来的人态度非常强硬,其中有一人说道“自家女儿惹出的祸事,竟然叫嫂嫂替尔顶罪,还敢妨害公务,不仁不义之辈。”
这几十年来,封应时就没见过敢对封家这般态度的人,一时还有些不敢相信,气得直哆嗦。
但又心中一凉,看这人说话像是站在柳氏一边的,便猜测这些人是封问心授意的,还是柳千重授意的,否则怎敢如此大胆,他喝道“你们是谁的人?”
那人又道“我等奉旨查案,再敢阻拦,连你一并拿了去。”
封应时脸上下不来,他上上下下打量那人,沉声道“今日之辱,来日必将加倍讨还!”
那人毫不畏惧的嗤道“你先与你兄长解释清楚,究竟是为何要窝藏罪魁祸首,置嫂嫂与相府的颜面于不顾吧。”
封应时想起那日封问心来这里说的那番话,顿时心中一突,有种有嘴说不清的感觉。
他突然就生了悔意,寻思着早知道会到这一步,当初就该将庶女交出去由封问心处置,如今非但保不住庶女,还使得兄长和柳氏对他心存芥蒂。
封问心来时,封应时就有些无言以对,目光躲闪。
还是他府中的管事,将今日来人拿走了姑娘的事笼统的讲了,却并不敢提封应时被人教训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别有用心,万一封问心没有那些想法,却被这些话提醒了呢?
封问心没有久待,见事已成定局,就打道回了府。
心里想着封应时那一副沉默不语的姿态难道是在怨怪他?
他陡然升起了一股怒气。
次日一大早,有许多人在帝京各街道沿街敲锣,高喊廷尉署将于午时在廷尉署门前当街公开审理白氏惨死一案,望各位街坊邻里有闲瑕时可备好烂菜叶前往监督,以证我北阴律法严明,绝不会姑息任何犯罪行径。
这一出让封问心和柳千重都始料未及,待他们听闻这件信息之时,帝京都已传遍了,还未到午时,廷尉署门前便聚焦了乌泱泱的人,一眼竟有些望不到头,许多人手里还挎着小菜篮。
封问心从侧后门偷偷摸摸进了署衙,颇为恼怒的质问任观言“谁准你这么做的?你置我相府的颜面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