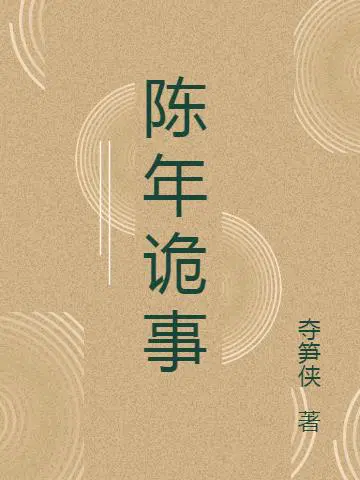再次醒来,果不其然又回到梦境中的客厅。
只是我环顾四周,发现红衣女人的头颅既没有在阳台,也没有在茶几上。
“嗯?”
我疑惑地左右看看,准备去妍姐的卧室,也就是红衣女身体所在的房间看看。
然而就当我刚走到客厅门口,突然看到红衣女就站在拐角!
它的头依旧包着黄纸,但此时却已经接到了身体上!
难道它恢复了?!
我瞬间瞳孔放大,心头腾起恐惧之前,我下意识地抬脚猛踹几乎和我贴脸站着的红衣女。
出乎意料地,它居然被我这么一踹就倒在地上。
而原本我以为已经长好的脑袋和身体,也在倒地后重新分家。
原来不是恢复了?
我连忙俯身查看,发现红衣女身体脖子处的伤口并没有恢复,刚才大概只是它强行把脑袋和脖子摁到一起。
“你还挺调皮。”我自言自语地去捡那颗滚到不远处的黄纸头。
可下一秒,那颗头却突然动了起来!
红衣人的头就像长了腿了一样,试图快速逃离我的手。
可惜它的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被我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我弯腰就抓住它披散到地上的头发,一把把整颗人头给薅了起来。
提着人头仔细查看,我才发现这人头的脖子伤口处,不知何时竟然长出来八根细如牙签的腿。
那八条腿此时正在拼命无助地摆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虫子。
嗯?
八条腿?
我突然眉头一跳!
我现在可还记得,当初从棺材里复活前,在那个奇怪梦境中的遭遇。
那梦境本身没什么,大约就是土蜘蛛和初代佐久间的回忆。
重点是在梦境最后,蜘蛛赠与我的那枚蜘蛛卵!
那颗卵我放入梦境之中,当时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事儿。
但等我再次回到梦境时,却发现红衣女的头不知何时居然把卵给吃了!
只是后面的事情太多,而红衣女把卵吃了之后,也没发生什么变化,我便不再过于关注这事儿。
可没想到,这次阴差阳错的黄纸糊脸,却让引出了后续变化!
我毫不怀疑这肯定是蜘蛛卵的作用,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土蜘蛛】应该是比【红衣女】强大的多的存在。
之前花子贸然进入我的记忆之中,就是被红衣女给狠狠阴了一下,最后迫于无奈才召唤了【土蜘蛛】的两条腿。
仅仅只是两条腿,就已经把红衣女打的惨不忍睹。
而红衣女吃掉蜘蛛卵后毫无变化,或许就是红衣女的灵异力量暂时把蜘蛛卵给压制住了。
现在因为某个巧合,黄纸的力量又把虚弱的红衣女给进一步削弱。
这就让原本在红衣女体内,被它所压制的蜘蛛卵产生了某些变化。
那么刚才人头和身体之间的结合,或许也是这八条蜘蛛腿的功劳。
难道红衣女把蜘蛛卵的力量给吸收了?
不对啊,蜘蛛的力量来自东瀛,而红衣女则诞生于约三百年前西南山区的某个洞穴。
这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这样也能融合吸收吗?
但如果已经融合吸收,那为什么蜘蛛的力量又会在红衣女被黄纸压制时,才显露出来?
这应该是失控的迹象才对吧?
还是说……红衣女之前其实一直在吸收融合蜘蛛的力量,而且已经吸收了一部分。
只是如今被黄纸糊脸后,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导致另一部分没有被吸收的力量开始失控?
不知道为何,我觉得这个推论十分可能。
倒不是说我有证据或者什么理论,纯粹就是因为红衣女现在和我的精神处于一种类似“绑定”的状态,我对它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红衣女就像与我共生的器官,我莫名其妙地就是觉得熟悉。
这远远算不上我已经理解了它的本质,纯粹就像一条养了很久的宠物,你虽然不懂它的语言和表情,但就是能从它的动作判断出它可能要干什么。
就当我站在走廊上思考着各种前因后果的时候,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
“叩叩叩”三次短暂的敲击后,屋内重回平静。
可过了不一会儿,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可是一个由诡异编织的梦境,怎么会出现敲门声?
难道是那个穿着病号服的老头?
嘿,还挺有礼貌。
不过我现在没心情搭理它,而是继续思考起红衣女人头的事儿。
昨天晚上我不撕黄纸,纯粹是觉得它不唱山歌挺清净的。
可短短一天,梦境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要不要撕开黄纸呢?我心中开始犹豫起来。
说实话,刚才看见红衣女的头和身体第一次重新结合,我心中是十分恐惧的。
当初为了对付花子,我用自己的血喂食红衣女,帮她恢复了不少力量。
如果不是后面【土蜘蛛】把它打的尸首分离,那之前的平衡早就被打破了。
红衣女人恢复力量会怎么样,这种问题根本不用问它会杀了我,然后离开。
如今被困在这个它最后编织的梦境中,纯粹是因为红衣女本身太虚弱了。
而它的虚弱正好和我达成一个平衡,让我在不用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使用它一部分力量。
我看着那八条细长的腿,心知平衡已经被开始被打破了。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想办法让这几股力量重获平衡!
其实仔细想来,之前的力量其实已经不平衡了,红衣女在逐渐蚕食蜘蛛卵的力量,假以时日,让它消化掉足够的力量,平衡可能瞬间就被打破。
现在这种情况,反而让问题暴露出来,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黄纸无疑压制了红衣女,让蜘蛛的力量开始占上风,如果我想平衡它俩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在蜘蛛的力量发育到和红衣女差不多时,重新撕开黄纸。
让失去黄纸压制的红衣女,与已经失控的蜘蛛卵重新回到某种平衡。
该什么时候撕开黄纸?
正当我犹豫之时,大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让人牙酸的金属变形声。
随后,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个身穿病号服,浑身干瘦,脸色铁青的老人,正缓缓向我走来。
它的脖子跟生锈的轴承一样,没法扭动。
老人也注意到了我,它挪动身子,把脸朝向我。
那双浑浊的眼珠此时正死死盯着我,让我心头寒毛直立!
一种恐怖幽深的晦暗情感,如同一只冰冷滑腻的手,突然从黑暗中伸出,死死攥住我的心脏。
哪怕在梦境中,我竟然也觉得有些呼吸不顺。
这一刻,我突然理解那些病人口中所谓的“恐怖”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下意识地摸向腰间,下一秒就摸了空。
我意识到这是梦境中,我不但没有铜镜,手枪什么的更别想。
“呃,你好?”我没话找话地说道。
病号服老头并没有回应什么,它死死地盯着我,哪怕它那浑浊的眼珠中没有一丝活人的神采,我也能从中感到巨大的恶意和怨恨。
它僵硬地挪动自己的双腿,蹒跚着向我走来,就像一个没有关节的提线木偶。
“尼玛!”
大意了,计划全特么被打乱了!
原本的计划只是借用红衣女的力量,来个一虎杀两羊,呃,我是说借刀杀…诡。
如今出了这个状况,原本应该最轻松的活,居然成了死局!
我倒是可以让自己醒来,可梦境里还有一个诡异病号服老头,以及一个看起来就要失控的红衣女,我这时候自顾自醒过来才是取死之道!
看着身形占据了整个过道的老人,我心中叹气。
这时候还纠结啥呀?直接干吧!
我低头看了看还提溜在手里的红衣女人头,伸手直接将糊在她嘴上的黄纸撕掉。
不过我留了个心眼,没撕完,只把鼻子以下部分的黄纸都给撕开,鼻子以上的依旧保留。
那黄纸在离开红衣女的脑袋后就变成纸灰,飘落到不知哪里去。
而红衣女的嘴发生了变化,原本只是没有皮肤嘴唇,纯粹两排大白牙的嘴,此时已经变得畸形又丑陋。
硬要说的话,有点像科幻电影《铁血战士》里,那种名为铁血战士的丑陋外星生物的嘴。
好在我提着它的头发,这张嘴暂时还咬不到我。
只是看着这张令人不安的嘴,我心中实在有些胆寒。
但事已至此,哪有犹豫退缩可言!
我咬着牙,将红衣女的人头直接扔向老人。
可红衣女的头撞在老人身上后就被弹开来,没有一丝进攻欲望。
“玩儿我啊姐姐!”
什么鬼,这时候掉链子?!
老人的身形甚至连停都没停一下,就这么一步又一步地向我走来!
它死死地盯着我,如同我也死死地盯着它。
舔了舔嘴唇,我心中念头电转。
实在不行就离开梦境!我心中打定主意。
这是最后也是最坏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选。
此时我已被逼回客厅,老头的脚步很慢,但步步紧逼,压迫感十足。
这里毕竟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熟的不能再熟。
这间客厅的面积本就不大,在放入一堆家具之后,能走人的地方实际只有一条路。
看着各种挡路的家具,我心知想跑都有点困难。
再困难也得跑!
我随手打开手边的立柜,如果没记错,这个柜子里是之前婶婶存放床单被罩之类东西的地方。
我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果然有几套叠的整整齐齐的床上三件套。
直接想也不想地就把床单拽出来,就像渔民撒网般,我直接把床单抖开,扔向病号服老人。
紧接着一个侧身,直接踩着沙发,以离他最远的距离快速跑回去。
然而这些小把戏似乎没太大作用,就在我和老人擦身而过时,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左臂上传来。
我扭头看去,一只手已经不知何时,如同一把铁钳一样钳制住了我!
“尼玛!”
我也发了狠,伸手从一旁餐桌抽出一把菜刀!
那把菜刀是之前花子为了恐吓我,从厨房拿来肢解“妈妈”的道具。
不过我没用菜刀去砍断胳膊,这把刀估计一时半会也砍不断。
我握着菜刀,转砍为削,顺着肩膀一路削下去,直接把老人住着我大臂的那条肉都给削下来!
胳膊少了一条肉,自然细了不少,趁着空档,我一用力,终于从老人那老虎钳一般的大手中挣脱出来。
“嘶嘶嘶!!!”哪怕疼的我龇牙咧嘴,脚上却没有慢上一步。
大约是因为菜刀并不算很锋利的缘故,那条肉并没有被完全削下来,而是有一部分皮肉还连在一起。
老人就像握住绳子一样,丝毫不愿意松手。
如果说撕掉指甲旁的肉刺,结果撕下来一条皮的痛感是1的话。
我感觉我现在的痛感大约是一万!
甚至因为太疼,疯狂分泌的肾上腺素让我反而不觉得有多疼了。
在硬生生利用体重,将那条连皮带肉的“肉绳”给拉断后,我已经有些看不清前面的路。
主要是疼的。
太他妈疼了,疼得我眼泪鼻涕一大把!
可此时哪还能顾得上这些,我连滚带爬的找到那颗正在四处打转的人头,咬着牙把最后一部分黄纸给撕了下来。
只是在稍微看清楚那人头的样子后,我还是惊得差点把它扔掉!
原本红衣女的双眼已经被挖掉,可此时双眼的位置上,却长着如同昆虫一样,密密麻麻的复眼!
那是蜘蛛的眼睛吗?
我已经没有余力思考这些,身后已经传来老人那僵硬沉重的脚步声,我没时间了!
“大姐!靠你了!咬死它!回来我请你吃鱼香肉丝!”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看也不看的将人头扔了过去。
这个距离不可能扔歪!
做完这一切,我松了口气,靠墙坐下。
爱谁谁吧,要是还不行,我就脱离梦境,反正还有一枚保命钱,不信没办法!
趁着这会儿功夫,我用衣角擦了擦糊在脸上的鼻涕眼泪,向不远处看去。
那个老人此时已经倒下。
红衣女的头此时正扑在它身上大快朵颐,我分明看到随着人头的进食,那蜘蛛的八条腿居然越来越长,从原本牙签大小,迅速膨胀到手指粗细,每条腿都有两节,而一节腿的长短至少有一根筷子那么长。
我又叹了口气,也不知这变化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