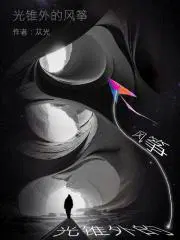“啊!这荒诞的人心。
啊连这死亡的盛景,亦要被榨干每一份价值。
啊啊!我城东李子坊,李明博就此参上!
啊博绝非沽名钓誉之人,就让博孤身结束这荒诞的闹剧罢”
他看上去像个诗人,语气深情而让人动容。
与第一名登台的年轻人不同,这博诗人他面貌奇古,给人一种老顽固之感。
他一定深信着自己说的话。
至少看上去如此。
他在无人期待中登上了高台。
结果。
又是一个小丑。
“呱“
它蹦跳着从台上,跳落在台下。
......
“啊?他们怎么这般积极?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情。”艾可可纳闷地说道。
裴焕表面宁静,内心如同塞入了一大堆不忍闻之物。
身处舞台核心,他的观丑位置最为贴近。
这一幕人间猎奇,几乎贴着他的脸放映,而登台的人并不知道镜光舞台的内里,还有一只权限的疯狗。
裴焕正趋于疯狂,人们比他更疯。
他运筹帷辍,推动事情一步步向自身所愿的情景发展。
眼前这群魔乱舞,在大的方向上并未脱离他的控制,甚至有加速的效果。
可是细节之处,却又与他想象的情景,有极大的不同。
至少,客人该是理性的博弈后,渐渐随着水温流速不同而失准,最后才无奈被裹挟其中。
裴焕看着不知何时艾可可,其庞大的身形让他内心生出一丝安全感。
还好,还有它。
还好,情况依旧可控。
思考了一会,他不确定地轻声说道:“也许,这是他们认为的机会?”
艾可可嗤笑道:“机会,手中无任何技艺,单凭着功利虚荣推动就登台献丑?这要是成了,五名城该毁就毁了算。”
裴焕心力还大多在观察那边,现在说话的他,仅仅是他留下一小部分预防意外的自主意识。
不理会老官熊的暴论,小半个裴焕平淡说道:
“这确实不成,内心无月目中无神手里无措身后无景。
这样无德无眼力无才无血脉相承托的四无皆具之人。
若是凭借登高乱呼,便能登台耀威,那才是明镜的失察了
不足论者,罢了”
艾可可大大的屁股砸在舞台上,菁水楼原本的舞台为之一颤,镜光舞台却未漏分毫。
它坐在裴焕身旁,却隐隐要比站立的裴焕还要高。
如此的生长速度,终有一时这为‘人’而造就的高城,就要承托不了它的体型。
为了防患于未然,裴焕打算此间事了回去后,他就迅速拟定一份《关于艾可可的减肥减食计划2.0强制性方案》
绝对不是眼前的一幕触动了他,让他担忧自身最后也会沦为身后无景之人。
艾可可明明已经是早熟的巨熊模样,声线却发育的相对迟滞,还是一副有五分童音的模样。
“汝不用担心,此处有吾,要想从这明镜下寻路,断不是此种取巧方式。
结实锤炼自身,成就四有,才是脚下生路必经。
汝还是要纵览全局。”
坐下来的艾可可说话都硬气了,仿若这明镜真的完全听他的一样。
他没有理会艾可可的颐气指使。
裴焕失笑,这些道理谁人不明白,不过的确这是微小插曲,自己还是要看着整体。
整体正稳中向好。
着急将这台上,当成快速阶梯的人,虽然在焦点中心往外看,似乎是所有的客人。
可一旦脱离了点状的视野,这些手中无措就急着登台的人,终究是无法代表客人的整体的极少数。
更多的客人,实则依然将自身包裹在黑暗中,观察着台上台下的其他人。
用伺机描述,倒算是贴切。
但却不一定得动。
动或不动,也许他们还未有一个方向。
他们犹疑着。
这也是裴焕想要的局面,失声者似乎很难逃避被裹挟被代表的命运,至少在这菁水楼里,裴焕几乎没有给他们其他的选择。
整件事情中,他们由于被裴焕主动切分,这个群体的结构性被降低,没有了更注重整体利益的喉舌,他们就失去了自体的‘人格’。
从客人的角度,他们全然这一片只能被动的泥沼中,案板上虚假选项选与不选差异不大。
当然一些选择可能会让当前的局面的崩解,只是那不是一个人选了就有用,更不好说选择的人是否能承受其代价。
裴焕引导着渊流,自身也随时可能被撕裂,可是将这混乱为主的渊流,注入他用心打造的‘河道’中,也是他正在勉力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着急的小丑,很可能在帮助裴焕。
他们是客人中极少数,却是浮在水面上的浪头之花,他们是牵扯注意力的发声人。
纵然他们会跌落渊流之中,甚至粉身碎骨。
当他们钻进了裴焕造就的河道,牵扯着一部分浪头浸润干枯河道时。被不断积攒情绪束在原地的渊流主体,很可能以为找到了一个低位,一旦它开始倾泻而下。
当‘高低’之位一旦确立,势便形成了,失声者的意见很可能再不重要。
那时也是裴焕的缰绳成形之时。
艾青是一个小滑头,艾可可是一个大滑头。
滑头组合将组织的工作任务,全部丢弃了裴焕后,开始当着裴官人的面开始摸鱼。
也许是先入为主,艾青比起上下限是两种棋的轮转棋,她还是更重要稍显简单的雀牌。
一人一熊,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了棋盘。
此刻又杀在一起。
在臆星熊的幸运加持下,艾可可很难输。可或许是它有意相让,好换取它更在意可肆意进食基本熊权;或许是艾青也是五名城运气倒灌之人,较之臆星熊也不曾多让。
一时间,竟然是艾可可赢得稍多一些。
裴焕不经意的瞟了一样他们的牌面,差点浑身一哆嗦。
这都是什么神仙牌面,一副雀牌怎么好凑出这样的神仙对局?
时间流逝,裴焕一心二用,一边关注局势,一边偷偷观棋。
他们快进快出,各种难以置信的上手胡屡见不鲜。
让裴焕他这个老臭棋篓子,两眼失去了亮度,他正逐渐失去了对雀牌的兴趣。
至少不能与他们玩了。
也许,该去找一个天生倒霉之人?
呵,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啊
裴焕暗自摇头,自己终究是想的太多了。
......
另外一边,登台的人稍稍多了一些,偌大的舞台已经不由一人占据。
慢慢地也开始出现一些手中有措的才人了。
群魔乱舞的现象有所平复,其中一些人更是带来别开生面的‘表演’。
菁水楼的人虽然才华是基本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才华完全在自身能力的甜品区。
基本都集中在音律舞艺等领域,最多再延展出诗歌杂技或是一些其他的融合特质。
可客人不是,他们来自五名城各坊。
所行路,所倚重的都各有不同,而且在整体比例上并无明显的失衡。
一些不适合舞台的路,被镜光舞台‘转译’后,竟然也有一番别致的风味。
例如擅长巧舌的商人,镜光舞台浮现了一个能够与之商人浮影,正在向正主无所不用其极的兜售着某物。
‘两人’知根知底,话术雷同,都在机关算尽试图攫取最大的利益。
‘吵’的不可开交,这边刚刚祭出屠龙宝刀,那边就是一个‘还要剑,这是不能再剑!’
事主可以自行中止这种滑稽的表演,可他或许也是上了头,在某种奇怪的好胜心左右下。
他定要让对面这‘人’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杀价之王,铁皮合成的公鸡!
‘船新’的艺术形式,给了台下的客人,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震撼。
‘你来我往’中,有人更期待了,有人也更恐惧了。
......
由谨慎铸就的堤坝,往往是在见他人走过无事后,就会缓缓地消融崩塌。
客人面前的这道坝,也在一系列不该被称为表演的表演中,缓缓彻底消融了。
而且这是一个结果,具体的过程被笼罩在黑暗中,每个人开始的时机更加的难以判断。
溃堤时,裴焕期待的势,就有了苗头。
现在,堤溃了。
看席中间的各条过道上,挤满了喧嚣的人群,黑暗中各人所见的范围都比较小。
只有彼此靠得比较近时,才能看清楚对方的表情,好在这种氛围中至少不会因为看不见,而出现踩踏的事故。
客人都逐渐忘记对舞台的忌惮,反而缓缓地将这当成一种机会少有的新奇体验,甚至开始期待着这个过程。
这样的转变,要多亏了人群中不少见的大儒们,他们对裴焕的帮助无以复加。
当然裴焕更喜欢,将这种行为归结为人的‘自适应’,并且他不打算感谢这些人。
当客人开始集体登台时,每一个舞台都几乎同时承载了千人时,焦点的模糊成为一种必然。
客人只能看清眼前的台上人表演,至于另外一面,或者只是稍远一些的台上人,他们由于失去了看席上的高阔视野,也就无法看清。
客人依旧是客人,可当前的他们,却依然不是场外的观众了。
而黑暗中有一双双明亮,却不会让人往阴暗处想的眼睛,他们成了新的观众。
他们是菁水楼的清白人,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内心也很复杂,没想到会有这个时候,他们待着看席上成了观众,而客人则需要自证登台。
真的是荒诞又滑稽啊!
因为台上人呵台下人,此刻的位置正式反转了。
失焦就找不到重点,菁水楼的人关注的人也不尽相同。
而找不到重点且质量参差的表演,即便是被称之为拙劣也算不得过份。
此刻的舞台,也第一次有些失去了它的魅力。
时间的刻度难寻,这一切在较远的人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式。
只有公式里面的人,还能看到眼前或有趣或是无聊的表演。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关注他们的人变少了。
这段时间很漫长,在整体上也较为无趣。
在确认溃堤的那一刻,裴焕的心思也逐渐从对客人的观察中抽离出来,仅仅留了一些以防止某些意外。
他的眼神,盯上了更高位置的字房,他一开始就明白,那里的客人大抵才是真正的重点。
裴焕的眼神晦暗难明,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
就在这场盛典中,真正博弈的几方都觉得不会出现意外时。
意外,还是来了。
又是一场没有预报的死亡。
这次死的人更多了,而这次死的人是客人们。
在客人都离席进行这场或自愿或有半分被迫的自证时,所坚持留在原席的客人。
就在场上一双双变得明亮的眼睛里,变得慢慢有点扎眼。
一种难以言语的逼迫感愈加的沉重,一些人即便内心千般不愿,还是在叹息中踏上了见证自己所重的路,于人前。
人后的人,也越来越少,他们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反而开始超越台上的人。
失声者最后的倔强,被悄然的重碾而碎。
毕竟事到如今,他们都明白,他们都已经深陷了自证的陷阱。
这虽然有些荒缪,可在这特殊的情景下,在裴焕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下。最重要是在本该与他们站在一起,此刻却用发光的眼睛盯着他们的其他客人们。
他们也明白必须该放弃一些东西了。
也许,那面镜子鉴查真的就是那些浮相。
他们这样安慰着自己,然后踏上了舞台。
他们大多是有措之人,所以大多并未出丑,而与案件无关阴暗,似乎也没有被镜子翻倒出来。
他们暗自松了一口气。
然后成了看向坐席的目光之一,既然镜子言行合一,我们又都与案件无关,你们又为何还不上台?
难道......
少数者越来越少数,他们所受到了压力被逐步增压。
一开始人群像是水库中不断承续升高的水体,需要有个破发的过程,需要慎重的寻找出处。这个过程比较漫长,登台出库的人却不多。
然后堤破了,人群变成了倾泻的洪水,灌进了这新开发河道,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河道那时是什么。
这里的时间反而看起来过得较快,高台成了被倾泻洼地,水流很快就挤满了整个河道。
最后,水库愈来愈高,好像没入了无法呼吸的真空。
真空里的每一滴水流,都仿若被暴晒着被一种外力试图将它们都抽干抽空。
弦被越绷越紧,第一个破窗重要出现了,他们用自身当成石子砸向了破烂的窗户。
最后,水没有抽到新河道里,却被暴晒蒸发了。
最后,他们选择了以死明志。
......
裴焕看着闯入舞台内相的陈竖,他的神情有些恍惚。
他还是失控了。
尽管非是全局;尽管无论如何看,他们都不必如此;尽管还有别的解释。
但这都大抵改变。
现在,他已经成了凶手。与在场的每一位被他领到帮凶路上的客人,还有做最后厘清的菁水楼众人。
第一次裴焕升起了一丝迷茫,他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尽管陈竖在汇报新的情况时,他的声音很小。
可依然没有瞒过艾可可的惊人听力,它拉着艾青没有多加思考,便靠向裴焕与他站在一起。
这是它的选择。
巨大的屁股,挤的裴焕一个站立不稳,裴焕被拉回了现实。
看着身旁的两人,裴焕的神情缓缓从惊愕又变回了坚定。
是啊,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至少要等事情做完,再论对错!
陈竖刚才说:“甲乙席客人,不愿下场登台者共一百二十七人,皆以自迫心脏而亡。”
陈竖看着站在一起三人,犹豫了一下,这才咬牙切齿说道:“我怀疑,他们就是凶手!此乃畏罪自杀!”
陈竖第一次在裴焕面前没有藏着自己的情绪,显露出了一种刻骨的恨意。
裴焕拍了拍他的肩膀,却没有顺着他的话立马表示同意。
显然,陈竖好像没那么在意,是否会累及无辜。
裴焕看着脚下的光滑台面,它也像一面镜子,上面清晰的倒映着他们的脸,四张脸四个不同的表情。
明镜其实揭不开所有的壳,也叩不了太多层的心关。
他们现在的脸上也有面具,有时裴焕连自己都看不透。
面具,那些死亡客人身上有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定有。
可是。
畏罪?明志?
那么,他们是哪一边的呢?
裴焕暂时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