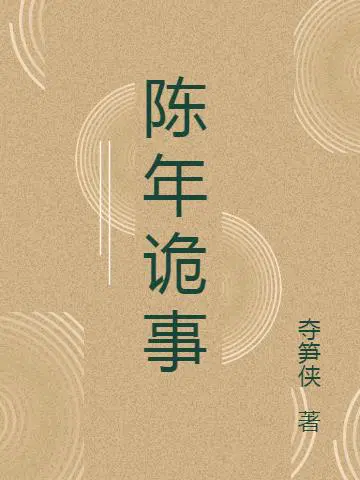石油佬呢?换座位了?
林明注意到我在看她,疑惑地问道:“怎么了?”
“额,石油佬跟你换座位了?”我问道。
林明可爱地歪头看着我,说道:“没有呀,我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吗?”
“对呀,飞哥,你记错了吧。”一旁的许如归也帮腔道。
我回忆起昨天上晚自习的时候,石油佬明明从我背后戳了我一下催我回家,今天怎么就换成了林明?
“不可能!”我坚决地摇头道:“绝对不可能!昨天坐在这里的肯定是石油佬,他晚自习的时候还戳我让我回家呢,你忘了?”
许如归关心地说道:“飞哥,你是不是没休息好?林明她一直在这里呀。”
“不对!”我坚持说道:“昨天明明……”
没等我说完,上课铃就“叮铃铃”地响起来,今天第一节是阿丽老师的课,所有人都乖乖闭嘴。
我表面上认真听课,脑子里却一团乱麻。
是我记错了吗?还是有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
一直到中午放学,我一直在回忆从开学到现在,这几天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头绪。
虽然越想越觉得撕裂,但我并没有想到有哪里不对。
我合上练习册,准备去吃饭,一张纸条从书里掉出来。
我捡起枝条,却发现字条上写着两个大字:回家!
回家?
什么意思?
和许如归约好一起去吃午饭,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还是砂锅土豆粉。
“阿姨,一大份土豆粉。”在窗口前,我对食堂阿姨说道。
“好嘞,回家看看吧。”阿姨说着,给我端来一份刚煮好的土豆粉。
“啊,什么?”我以为刚才听错了。
阿姨也奇怪地看着我,问道:“同学,一份不够吃吗?”
“没有没有。”我端着土豆粉去和许如归会合,脑子中却一直想着这几天的怪事。
“飞哥,怎么了?回家吧。”许如归关心地问道。
“啊?回哪里?”我迷茫地看着许如归,她让我回家?
“我看你今天上午一直挺没精神,想问问你怎么了。”许如归解释道。
我点点头,不知道遇到的怪事该怎么和许如归说。
吃完饭,我把餐具送回去,发现餐具回收处原本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标语,不知何时变成了“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但等我揉了揉眼睛,却发现标题又变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上个厕所,你先回去教室吧。”我笑着对许如归说道。
等她走远,我立刻拔腿就跑,因为有走读证,门卫并不拦我。
坐上444路公交车,车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我和司机。
怀揣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到站下车,往家所在的小区走去。
此时小区里安静的过分,但我无心深究,只想赶快回家。
推开家门,我发现爸爸妈妈依旧坐在客厅看电视。
见我回来了,妈妈笑着起身问道:“晓飞,你回来了?饿了没?跟你留的有饭!”
不知为何,我的手有点颤抖,声音也连带着颤抖地说道:“妈,我…我饿了。”
妈妈慈爱地说道:“好,晓飞你等一下啊。”
连这句话都一模一样吗……
过了一会儿,妈妈端出来一盘菜和小半个馒头。
那盘菜是一盘炒豆芽,馒头被吃的只剩小半个。
那是我开学第二天时的早饭。
见我盯着这盘菜不动筷子,妈妈一脸关心地问道:“晓飞,怎么了?不合你胃口吗?”
果然,每句话都一模一样。
我看向妈妈,颤抖着问道:“妈,你…你是真实存在的吗?”
妈妈愣了一愣,随后笑着温柔地对我说道:“当然了,晓飞,我是你妈妈呀。”
听到这句话,无数记忆忽然如同决堤的洪水,冲击着我的心灵。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悲伤像深秋的雨,连绵不绝地从我眼中流出。
“你…你不是我……”我哭着看向她。
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我连眼前这个女人的长相都看不清。
因为我根本记不清妈妈的样子,我从小就失去了她。
她不是我妈妈。
我没有妈妈。
我叫陈晓飞,是个孤儿。
“不是什么?晓飞你怎么哭了?”
为什么我明明看不清她的长相,却能感受到她的关心和爱护?
她是假的才对,不是吗?
我抱住了她,哭着喊道:“……妈妈!”
我努力感受着她的温暖,心中却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我在我人生中最快乐一段时光中,加入了我认识的所有友人。
原来我的梦想不是什么买房子,也不是什么救叔叔。
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爱我的父母,关心我的朋友,聊得开心的同学,和努力就有回报的生活。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所有。
但我没有这些。
原本属于我的家庭早就支离破碎。
爱我的父母早已过世。
关心我的朋友已经分别。
聊得开心的同学已经去世。
如今过的都是险象环生,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些才是真实。
“妈妈,”我又抱了抱眼前这个我连相貌都看不清的女人,努力笑着对她说道:“我要去上学了,下午有课。”
“嗯,那你早点洗洗手脸脚睡觉啊。”妈妈嘱咐我。
她似乎没听懂我想说什么。
似乎又听懂了。
我放开手,看着她去了厨房。
我再次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所谓的“家”,其实就是叔叔的家。
电视上那场节目,我也有印象,那个女孩子是我曾经很憧憬的一名偶像。
这场节目是她出道的首秀。
但那次我没看完这个节目,婶婶就把遥控器拿走换台。
再往后,就再也没看过这场节目的重播。
原来,她的首秀已经在我的心中补完了吗?
我转身走向表姐,不,应该是妍姐的房间。
推开门,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面墙打了一套高到屋顶的吊柜,中间是一张床,靠窗户的地方是一张书桌和衣架。
一具被剥了面皮,穿着血红色嫁衣的女人尸体静静地躺在床上。
它没死,我能感觉到。
但它也很虚弱,虚弱到为我编织的梦,也全是靠我脑中最强烈的渴望来作为素材。
或许我该谢谢它,谢谢它为编织了一场如此美好的梦。
但梦终究是要醒的,当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梦以后,就再也骗不了自己。
“谢谢。”我对红衣女人点头致谢。
随后拿起一盏摆放在床头的灯,那是一盏造型古朴的油灯。
此时油灯中的油已经烧的见底,看上去马上就要烧完。
“呼”我轻轻一吹,油灯就被吹灭。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本能地,我就知道这么做有用。
或许是这个红衣女人的记忆和我已经融为一体也说不定。
油灯熄灭,我的眼前一黑。
随后睁开眼,映入眼帘的,还是熟悉的天花板。
我又从复活点刷新出来了。